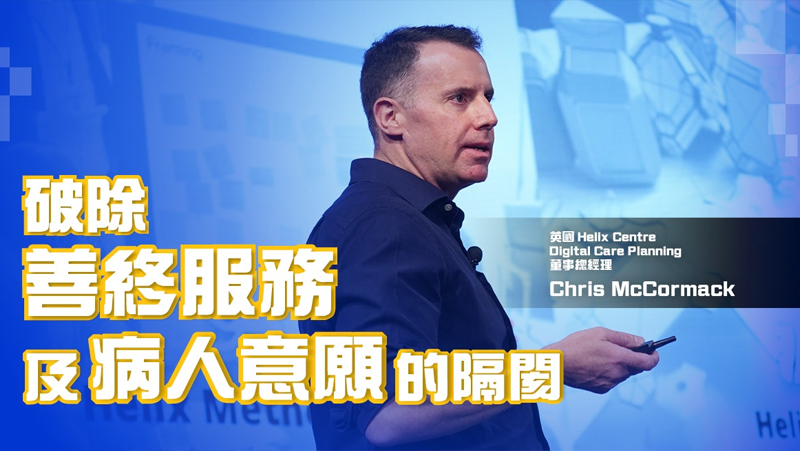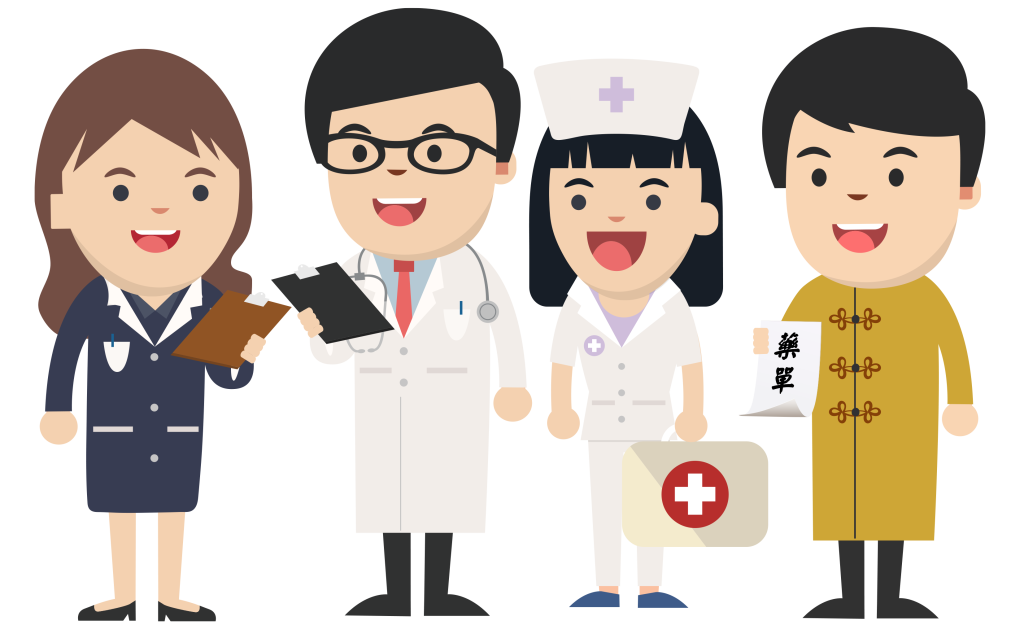【打造以「家」為中心的醫療】一名醫師親臨日本「在宅醫療」現場:
生命最終,醫療只該是「支援」
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:40 歲的你,整天在北部打拚,是否曾經為了陪伴親人回診從台北趕回中南部,請假一整天?70 歲的你,獨自一人的夜晚,發燒不知所措,不想打擾兒孫,只能撥打 119 叫救護車。
「阿伯,醫師說你不能再吃東西了!」C 又在偷吃了。
腸胃科醫師說沒有辦法繼續替 C 治療食道癌了, 要請「安寧」的醫師來看看。C 想回家,因為他想奪回吃的自由,在僅剩的生命時間內。C 決定帶著氣切管和肚子上的一條灌食管(也就是經皮穿刺胃造口)回家。
第一次跟 C 見面,C 問:「我可以從嘴巴吃嗎?」
等不到醫師同意,回家後的 C 已經就餐桌定位。水餃、餛飩、滷肉、鹹豬肉,還有零食、甜點,無肉不歡。C 的太太手藝很好, 夫妻經營過一家小吃店, 生意不錯。每次往診,我們都故意錯開午餐時間,否則就無法抽身,非上座吃一頓不可。一杯茶、一些茶點,往往是居家訪視的固定補給。
我一個月至少一次會幫 C 換一支新的氣切管。出院不久,C 肚子上的胃造廔管早已不用,百分之百用嘴巴進食。就這樣度過了半年,直到 C 陷入昏睡為止。
食道癌的病人真不能吃東西嗎? 有時候,我們會忘記 C 是食道癌的病人。照顧 C 的半年裡,我對醫學上的診斷產生了問號! 和一般的認知落差還真不小。今天吃了什麼? 下次要吃什麼? 才是我照顧 C 半年來居家醫療的重點。後來我才知道, 這種支援在家生活的醫療, 在日本被稱為在宅醫療 。
到底什麼是「在宅醫療」?
家裡的瓦斯沒了,一通電話,瓦斯行就送到厝裡;家裡的馬桶壞了,自來水馬達壞掉,一通電話,水電工就上門;可是家裡有老人家生病,身體不舒服,出不了門,該怎麼辦? 家裡有癌症末期的人發生狀況,就是一通電話,叫 119 嗎?
老一輩的人常說「請先生來往診」,「往診」就是醫師會到家裡看病,但現在台灣社會,幾乎看不到這樣的景象了。早年因為醫師少、看病貴,不少人把小病拖成大病,非到真正嚴重到快不行了,才拜託先生來厝裡,因此,早期的往診,以急症較多,現在已經是慢性病的時代,醫師到家裡看病的內容,和過去應該有所不同了。
台灣 2018 進入高齡社會,65 歲以上老人比率超過 14 %。再過十年就邁入超高齡社會,和現在的日本一樣,老人比率超過 20 %,換言之,五人有一人超過 65 歲。年紀大了, 出門看病總有不便,是不是有更好的支援辦法呢?
醫師到家裡看病在日本稱為「在宅醫療」,在台灣有人稱為「居家醫療 」。不過兩者還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,對日本人來說在宅醫療是一種較前衛新穎的醫療概念, 定義是, 支援在家生活的醫療或健康照護手段。
在日本不管是不是罹癌病人、是不是末期重症, 只要有失能、失智或就醫不便的老人,甚至小孩,都可以接受「在宅醫療」,在宅醫療的各種服務,涵蓋醫療與長照體系、服務的給付和方法的推廣,並有財源來自醫療保險、長照保險以及地方政府或民間財團的資助。2012 年日本國家政策確立推動社區整體照顧後, 在宅醫療成為「社區整體照顧」成功推動的必要條件之一,在宅醫療不僅是概念,也是政策目標。
「居家醫療」在台灣仍是一個嶄新且有些陌生的詞彙,來自 2015 年全民健保推出以基層診所為主的一項試辦計畫——「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試辦計畫」。2016 年升格為「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」, 擴大為醫院也可參與,但需要組成團隊,同時服務對象也刪除身分限制。然而,這仍只是一種健保給付的計畫而已,並未成為政府的政策目標。 1995 年全民健保開辦之初,已經有給付護理師到家(包含機構)更換管路為目的的「居家照護」,也是屬於「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」的一部分。相 對於日本行之多年的在宅醫療,台灣的居家醫療尚有很長的路要走 。
到底「在宅醫療」如何在日本發展起來的? 首先,有關在宅醫療一詞的來源,有一說是在一九九四年,東京的柳原醫院為了照顧千住地區下町的居民,推出「24 小時巡迴型在宅照顧 」,這是一種結合醫療與照顧的全天候社區到宅照顧服務。透過居家護理師與照顧服務員搭配的小組,每天分為四班,在千住地區內巡迴。當時,院長增子忠道醫師在國會答詢時,即正式使用了「在宅醫療」這一詞彙。
現代日本在宅醫療的發展概念,大多以 1981 年佐藤智醫師在東京成立 NPO 組織ライフケアシステム(Lifecare system, 簡稱 LCS)開始。LCS 由家庭醫師提供 24 小時服務,也就是以「診所」為基礎的在宅醫療。
1970 年代,佐藤醫師便認為「疾病是在家可以治好的」和「我們自己的健康要靠我們自己守護」。當時,日本的醫療保險制度沒有給付居家醫療,也不存在長期照顧的保險(介護保險),於是佐藤便提出 「大家的健康需要大家互相幫忙」的互酬性概念 。進而成立 LCS,採取會員制的家庭醫師在宅醫療與健康管理制度。
不只是看「病人」,而是以「家」和「社區」為中心的醫療
在宅醫療既然是一種支援在家生活到最後的健康照護行為, 因此,不僅要照顧生命末期,也要積極預防慢性病併發症,以及失能、失智的退化,支持在家生活,好好終老。日本四國松山市蒲公英診所的在宅醫療達人——永井康德醫師常說:「在宅醫療是 讓每個人『活出自己』的醫療 。」
在宅醫療和醫院醫療最大差別在於空間,也就是醫療環境的翻轉。接受醫療服務的人對此感受特別明顯。比方說,同樣住在社區內,在「自宅」接受在宅醫療利用者,可以維持原本習慣的生活方式,但是入住「機構」的在宅醫療利用者,多少需要改變既有的生活方式。
當我們說, 希望創造一個「在地老化」(aging in place)的社會時, 指的就是「在地終老」的環境, 讓長輩在盡量不改變既有生活模式狀況之下, 迎向生命的最後階段。因此, 與其說在宅醫療是以「人」為中心的醫療,不如說是以「家」為中心 ,以「生活方式」為重心的醫療。因此,實際從事居家工作的醫療人員,所見所聞的生命故事絕對比連續劇還豐富。
「這一次,我們沒有裝上鼻胃管」
「余醫師,我媽的鼻胃管又掉了,我不敢自己裝回去。」簡訊的那一端,傳來家屬的呼叫。
「好的,我中午前過去看看。」回覆訊息的同時, 也透過雲端平台,告訴負責案家的居服員督導,然後便飛快出發前往案家。督導提醒我,因為 今天不是上班日,醫院的居家護理師不會出來處理「拔管事件」。
「一個不留意,鼻胃管就被拔掉了。」兒子說:「偶爾她也會吃一些東西,但我擔心她會嗆到,所以不敢給她吃太多。」
沒有直接裝上鼻胃管,我們嘗試先將增稠劑加入果汁,用湯匙慢慢餵病人 B。
觀察 B 吞嚥的情形,其實沒有太大問題,難怪會自己拔掉管子。雖然進食慢,稍微活動就喘,但相信病人仍喜歡自己經口進食。很快的,兩百 cc 的黏稠果汁一下子就喝光光了。 這一次,我們沒有裝上鼻胃管 。
幾天後,從聽說兒子找來居家護理師把管子裝了回去。理由是, 他一個人照顧實在很累,無奈居家服務只提供「兩天一次」的支援, 在「吃」這件事情上,實在愛莫能助。
一個月前,我第一次拜訪 B,由於多重慢性病加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, 再加上失智, 她幾乎是全天臥床, 而且反覆的肺炎住院、出院。如此二、三次的照顧循環,讓獨自照顧的兒子身心俱疲,所以在居服督導的安排下,我們才有了第一次的接觸。
根據研究,75 歲以上的日本人(後期高齡者)到死前,男性會經歷三至五次、女性五至七次的照顧循環(care cycle)過程。第一次見面,我便跟 B 的兒子說明, 照顧循環的情形會一再發生,我們必須跟其他家人討論,什麼時候放手 。否則以現代的先進醫療,如果沒有癌症的話,人幾乎可以沒有生活品質地一直活下去。這一次住院能幸運的離開加護病房,下一次可就不一定了。
拔管事件幾週後,我的 LINE 又響了起來:「我媽不太對,能來看一下嗎?」簡訊這麼說。
事實上,台灣家屬很少會主動打電話給醫師,即使每次留下名片時, 我都會特地告訴他們,不要客氣,有問題就聯絡我 ,但會打電話的幾乎不到百分之五。如同日本式的在宅醫療,強調 24 小時可以應付案家的需要,這是「在宅療養支援診所」的基本條件。但要如何應付? 其實每個地方的作法不同, 讓對方安心卻是最高指導原則 。後來,我盡量以 LINE 的方式留下可以跟我連繫的管道。
上午,我拜託居服員督導先去查看,同時也請案家通知醫院居家護理師。「居家護理師叫我們送醫院! 聯絡過了,跟以前一樣。」簡訊這麼回覆,有點無奈。
下午,居服員督導很緊張的來電,說病人 B 已經昏迷了,但兒子還是希望醫師親自來看看再判斷。夜間我趕赴 B 的家中,她的嘴巴張大、瞳孔放大,對痛覺無感,還有發燒。不停發出的呼嚕呼嚕的痰聲, 有點嚇人。兒子倒是異常冷靜,或許是看多了,只是灌食沒有停止。
「請停止灌食,通知所有人回來。」
第二天,停止灌食的病人依舊嘴巴張大,瞳孔放大。停止灌食一夜後,昨晚嚇人的痰聲已經沒有,家人都回來了,眼眶泛紅。第三天早上,女兒來訊息通知我,B 已經沒有痛苦。啊,這就是平穩死!
當時唯一的醫療處置,是請他們停止灌食。 生命最後階段,醫療處置都可以停止,但照顧的工作卻不能停 。
生命末期需要照顧和陪伴, 醫療只是支援的角色 。從事安寧工作者,就像領航人一樣,陪伴著準備前往下一站的人們。我時常跟家屬說明,不要勉強生命,生命最清楚下一班車什麼時候會來。醫者應該要讓家屬清楚方向,才能讓他們做出對陪伴生命死亡最好的決定。